他們在島嶼寫作:文學大師記錄片
他們在島嶼寫作:文學大師記錄片 2011/03月號 印刻文學/提供【楊照/文】
一、
那是一個特殊的時代,因而產生了特殊的文學。或許應該說,那是一個特殊的時代,因緣際會文學在其中扮演了特殊的角色,以是創造了不同的、深刻的文學意義。
那是一個離亂的時代,離亂是那個時代最突出的性質。長達十幾年連續且愈來愈絕望的離亂經驗,鋪在那個時代的底層。先是中日戰爭,接著擴大為世界大戰,大戰結束立刻又引發內戰,內戰中,許多青年跟隨潰敗的國民政府,到了台灣。
到了一個陌生的海島上,遠離了家園,更遠離了原本的親族、地域社會紐帶。海島是離亂的終點,卻又不是。是終點,因為無處可以再退了,海島的背後,只有汪汪無垠的太平洋。不是終點,因為對岸的解放軍還是可能打過來,帶來不堪想像的變化。
離亂帶來雙重的心理壓力。離亂中的人最需要安慰,最需要有可以信任可以依靠的人在身邊;然而離亂卻同時將大家從可以信任可以依靠的人身邊拉走,更糟的,那樣的離亂情境使得任何人與人之間的緊密聯繫,都被投以懷疑、敵意的眼光。
風聲鶴唳下的國民黨,眼睛裡看出去,任何一個自主發展的組織,都像是共產黨的地下祕密單位;任何一點對於前途惶惑的表達,都一定會打擊民心士氣。這樣叫那些孤零零又不知明天在哪裡的人要怎麼辦?
幸好,還有文藝這麼一條曲曲折折的小路。國民黨檢討大陸挫敗時,認定了共產黨的思想工作,尤其是運用文藝媒介影響青年這一塊,是個關鍵。延伸的推論當然是應該在「反共基地」加強文藝戰鬥,擴張的文藝政策,讓來到台灣的青年,有了一點喘息的空間。
他們可以藉由文藝,尤其是文學,來打造新的人際紐帶。文藝、文學是相對安全的結社理由,而且文藝、文學能夠在人與人之間產生特別緊密的連結。
那個時代產生的文學社團,很難用今天的概念來理解。五○年代的詩社,六○年代的文學雜誌,其內在同人同志精神,有著驚人的強度。那樣的文學同人,幾乎就是參與其間諸人的首要關係。他們沒有家庭、他們沒有親族、他們沒有從小一起長大的朋友。這些原生性更強、聯繫更緊密的關係,隨著戰爭離亂都斷掉了,而且無望恢復,於是衍生性的興趣團體,就變成了他們僅有的核心關係了。
今天我們的「同人」、同好團體,是眾多關係中的一環,和這些眾多關係並置並存,互相重疊也互相競爭。「同人」之外,我們有家庭、有親戚、有同學、有同事、有朋友,但對於許多五○年代開始寫詩的青年來說,除了軍中同袍,詩社的「同人」就是他們關係的一切。
他們在那裡找到依賴,在那裡彼此摸索表達情感的方式,在那裡互相扶持一起成長。底層最根本的,自然是一種相濡以沫的需求,不過文學給了這種需求特別有利的發抒,倒過來,這種需求也給了文學創作特別有利的刺激。
因為是文學,所以他們能夠摸索、嘗試打造出一種新的語言,專門因應他們現實存在狀態而來的語言。他們需要一種語言,一方面可以傳遞惶惶恐懼、混亂不安、前途茫茫感受,另一方面卻又不會被扣上「打擊民心士氣」、「傳播失敗主義思想」帽子。這種潛意識的需要,配合互相的影響,他們開始向詩的語言,相對模糊凝重的語言偏斜,而且很快又在所有的詩的流派中,找到了「超現實主義」為其認同對象,不是偶然。
他們進一步相濡以沫的互動中,開創自己的感情結構。儘管用的是白話中文,又積極吸收模仿西洋的語法,然而現成的中文或外語中,都沒有可以確切對應到他們特殊情緒表達需求的成分,他們靠著討論文學,靠著徹夜聊天,靠著密集書信往返,更靠著不斷書寫及反覆交換作品,讓一顆被時代折磨得空洞枯萎的心靈,慢慢飽實,成就自我。
這些飽實的心靈,寫出了飽實的文學作品。貧乏壓抑的環境下,台灣五○、六○年代的文學,卻意外地傑出,經歷幾十年光陰移異,依然閃耀著動人的光彩。
這樣一代文學作者,這樣一種特殊的時代背景,值得記錄,需要記錄。
二、
林海音、周夢蝶、余光中、鄭愁予、王文興、楊牧,六位作家基本上都屬於這個時代,或者該說,他們都是在那個時代氣氛包圍下,完成了自我文學理念的尋找,並且打造了文學與生命的密實關係。
他們的作品,繼續流傳,從來沒有真正消失過。現在的讀者不需花費太多的力氣,都可以找得到他們的作品,甚至不需經過刻意的安排探詢,也可能在各種情況下遭遇他們的作品。
那,為什麼要替他們拍紀錄片?紀錄片所要記錄的究竟是什麼?擴大一點問:紀錄片所要成就的究竟是什麼?
首先,要記錄塑造他們文學根源的那個時代。讓讀者感受到:我們讀到的一首詩、一段札記、一篇小說,其實不過是他們生命關懷映照下的產物,作品底下有人,人的底下,有其他的人,有許多同輩生命交錯組構成的豐厚襯墊。
讀那一代作家作品,這種襯墊的還原呈現,格外要緊。讀今天青壯代作者,他們生存的條件與境遇,和我們基本相同,我們很可以單純運用自然的同理心去接近他們所要表達的文學意念。但若是以這種態度,不經提醒不經準備地去讀五○、六○年代成形的作家,我們必定會錯失他們作品中內在最重要的訊息,將我們想當然耳的以為,當成是他們作品的意義。我們將讀不到讓他們痛、讓他們悲、讓他們喜、讓他們迷的真正人間情感。我們讀了,卻沒有讀到。
還有,今天青壯代作者,文學是他們諸多日常活動中的一部分,一小部分。不在意不理解他們是什麼樣的人,過什麼樣的日子,對進入他們的作品,不會是那麼龐大的阻礙。
那一代的作家,文學是他們安身立命的根本,文學是他們探索乃至於證成自己是個什麼人的根據,不知道他們是什麼樣的人,也就無從掌握他們作品了。
紀錄片要做、可以做的,是透過人來鋪織時代,又回過頭來用時代剪出清楚的人影輪廓。人與時代辨證互相詮釋,彼此燭照,給作品一個可以安放的意義位置。
三、
六個作者,對文學同等專注癡迷,卻發展了和文學完全不同的生命關係。
我們必須知道王文興創作之「慢」,才能了解為什麼唯有「慢」是閱讀王文興作品的基本方法。「慢」意味著不只是速度,更是專注的條件,「慢」讓我們靜下來追究,文字為什麼如此組構;「慢」讓我們幽微思索,文字轉達的情感的來龍去脈。客觀的文字擺在那裡,卻會因為主觀的閱讀速度,而顯現不同厚度的生命經驗。
「慢」也不是一個抽象的速度概念,可以在影像記錄中具體化。知道王文興一個小時寫二十個字是一回事,從記錄畫面中看到他反覆近乎暴力地和形成小說作品的每一個字掙扎,是另一回事。王文興不只是一個和你我不一樣的怪人,他是一個怪得有其充分道理的人。他的道理,逼我們反省自己視之為正常的「快」。
楊牧用半世紀持續不斷寫出的詩,建構了一個與現實生活平行存在的浪漫宇宙。在那個宇宙中,存在著各種角色各種聲音,而每一個角色都比一般現實的人有著敏銳十倍百倍的感官,察覺最細微的光影挪移,登載最飄渺的心緒跳躍;每一個聲音都構成一種獨特的節奏,音樂之前的音樂,幾乎沒有一個雜音,沒有一個草率失誤的雜音。
和他建構起的浪漫宇宙相比,現實如此不純粹,充滿了粗疏大意。要能夠讓楊牧的作品把我們帶入那更純粹,表面平和卻又含藏內在驚悸力量的世界裡,我們可以先看到楊牧如何沉靜地、安穩地排除現實的干擾,所有的戲劇、一切的爆裂轉折都從生活中消退,只存在於他所閱讀及所創造的文學裡。我們驀地明白了:現實的平板與詩的浪濤洶湧,非但不矛盾,而且還是最理所當然的一體兩面。
四、
鄭愁予是「抒情浪子」的原型。在他早期代表詩作中,近乎神奇地將歷史悲劇的離散與無家可歸,改寫成一種生命自我選擇的喜劇。無法停留在一個定點、一個關係、甚至一個記憶上的人,他浪遊來去,那無著的生活方式,正是抒情歌唱的前提。或者說,他沒有其他可以依恃,只剩下抒情的歌唱,因而使得他的歌唱分外動人。
追溯鄭愁予的經驗過程,看到他曾經看到的海港,異國的街道,我們逐漸接近了那浪子原型的來由。在鏡頭上,他自在地進入各種不同環境中,更重要的,自在地進入不同人的生活中,又自在地抽離,他和環境之間,他和別人的生活之間,似乎並不存在絕對的界線,他總是在又不在。我們親眼目睹他這樣獨特的存在形式,飄忽卻溫柔,溫暖卻疏離,於是我們進一步體會了,那些浪子的歌唱,不是語言遊戲,而是鄭愁予提供給一個離散時代的難得藥方,只有具備他那樣存在情調的人,才有辦法提供的藥方。像是余光中的詩中寫過的句子:「我是一個民歌手/我的歌是一帖涼涼的藥/敷在多少傷口上」(〈民歌手〉)。
余光中在紀錄片中的主要形象,不是民歌手,而是「壯遊者」,從西方浪漫主義汲取養分,從另外一個方向,轉化了歷史悲劇帶來的命運。「壯遊」的背後,是從宗教背景中昇起的「朝聖」(Pilgrimage)概念。求取救贖,就應該選擇一個遠方的聖地,下定決心,忍受折磨,堅決勇敢地朝聖地前去。聖地目標固然重要,路途中所經歷的考驗,最痛苦最恐怖的考驗,同等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經過了「朝聖」考驗,人於是蛻變成忠誠合格的基督信徒。
這樣一個概念,到了浪漫主義時代,化而為拜倫筆下哈洛德的經歷。他的「朝聖」乃是對於各種歷史與自然奇觀的巡禮,去到非常的地方嘗試非常的感官刺激,於是一個平庸的青年,成長化身而為生命豐沛滿溢的詩人。是之為「壯遊」迷人的浪漫價值。
余光中用詩把離散「壯遊化」了。面對不得已的家國傷痛,他既不逃避也不無奈哀嚎,而是予以個人私我化,成為自己的考驗。必得走過這些考驗,人才成長為詩人,用詩將這些經驗固定凝結下來,予其普遍與永恆的意義。
五、
周夢蝶曾經是台北最美麗的街景,武昌街上一方小小的書攤,攤上擺了各種詩刊詩集。詩人坐在攤前,以其生命姿態和那些書相呼應,卻又和賣書的生意保持若即若離,在亦不在的關係。熙來攘往的人群當然還是多的是為名而來、為利而往的,但在那一條街上,可以確定總還有些人不為名也不為利,為了詩與文學來來往往。
我們看到,並且因而相信了,一種詩人生命的可能性。他們活在俗世間,但俗世真正的意義卻在於鍛鍊各種透視拒絕的方法。詩人建構起自己的「孤獨國」來,然而弔詭地,「孤獨國」真的不是為了隔絕獨居而打造的,「孤獨國」是為了引領所有夜中不能寐的寂寞靈魂而寫的,讓他們得以從忍受寂寞襲擊到享受孤獨的洞見。
周夢蝶以詩為那個時代龐大的寂寞思考,將感官的痛苦轉化為透亮的說理,那亮光刺著眼睛,使人不得不在亮光前遮起眼來,於是在遮眼的瞬間,看見了自己內在某種原本不以為我們可以看得見的風景。
林海音則曾經是台北最溫暖的陽光中心。坐鎮在《聯合報副刊》,《純文學》雜誌與出版的背後,不斷地送出關懷鼓勵,讓原本不知道自己是作者的人,知道了原來自己是個作者;讓原本不確定文學和自己有多緊密關係的人,領悟了文學竟是自己活下去最大的動力。
編輯是文學的拓荒者,又是文學的守護者,守護著所開發出來的,又不斷越過已經耕耘的田地邊界,探入更廣大的荒野。編輯每天打開信件,閱讀一篇篇寄到手上的作品,放下作品,拿出信紙,開始寫一封封的信,聯繫作者,將所有作者攏入一張大網中,大家彼此連結,結成了文學的社群。
林海音代替了許多青年永遠見不到了的母親。給他們一個以文字文學包圍環抱的家庭,給他們許多心靈的兄弟姊妹,對抗那個離散時代尖刻的寒冷。
六、
記錄本身就是一種詮釋。尤其是面對一個已經逝去的時代,面對眾多即將消失的記憶。
選擇記錄在那樣的時代中浮現的作家與作品,是一個清楚的立場。那個不一樣的時代,從不同生命體驗中產生的文學,不應該用今天現實想當然耳的方式,草率地閱讀。那樣文學被擺放回其創作者的具體人生觀照中,我們領會其珍奇影響,看到了那些我們自己永遠寫不出來,卻可以和他們同悲同喜的獨特內容。...(未完,更多內容請見《印刻文學生活誌》91期三月號)
文章引自:http://www.sudu.cc/front/bin/ftdetail.phtml?Part=3070000091&Seq=727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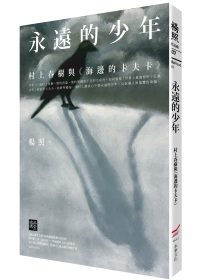
近期迴響